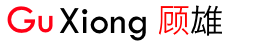滨湖尼亚加拉地区有长达五十年的雇佣国际移民劳工的历史。现在,很多人从牙买加和西班牙来这个区域的果场上工作。作为我“移途记忆”项目很重要的一部分,顾雨、斯考特和我已经来过尼亚加拉两次进行摄影。我们来拍摄人们在不同的果场上的日常生活,并采访这些人。我们去年夏天来这里的时候,主要是进行采访。这一次我们再来是为了记录他们每天的生活和果场的日常。
8月22日,我们分别从温哥华和洛杉矶坐凌晨6点的飞机出发,抵达多伦多的时候是下午两点。我们在机场租了一辆福特SUV,开始了旅程下一段——前往滨湖尼亚加拉。从多伦多到滨湖尼亚加拉的旅程据说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但是因为多伦多的交通状况,我们花了三小时才抵达滨湖尼亚加拉。下午6点的时候,我们到了苹果木家庭旅馆(B&B)。这次旅程我们一直住在这里。当我们开到旅馆时,我注意到旅馆是完全被果地环绕着的。旅馆的主人是简・安德鲁。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简始终在帮助这个区域的国际移民劳工。三年之前,我通过布鲁克大学的罗德曼・霍尔艺术中心的一位策展人认识了简。通过简和她的组织,我们认识了十二位我们可以单独采访的人。我们去年的滨湖尼亚加拉之行结束后,我们前往牙买加,在其中三位工人的家乡采访他们。
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记录劳工从日出到日落,全天的生活。之所以特地选择在8月份前往,是因为8月份是生产季节的尾声,果园上最忙的时候,也是劳工们准备返回家乡的时候。为了拿到采访的许可,我们首先要获得果场主的同意。简把我们介绍给了三位果场主,以下用A,B和C指代他们。A来自瑞士,1970年代移民加拿大。他是一位独立果场主,不是文兰种植合作企业的一部分。他对自己果园的生产运营有科学的、有效的思考,并建立了自己的经销网络。这个经销网络已经存在有将近50年。A努力地避免浪费,并研究出很多方法来确保自己的产品从种植环节起就获得成功。A也是一个思想开放的人,他完全不介意我们拍摄他果园里的工人。一般来说,获取果园主拍摄许可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是在A这里,没有这样。
B是我们接触的第二个农场主。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就拥有这个地区最大的果园,并把这个果园建得越来越大。当我问他,他的果园究竟有多大时,他只用简单的一个字回复了我,“大”。去年我们访问了他的果园,并和他的儿媳D交流,她同意我们采访农场工人和在他的土地上摄像。今年,B的兄弟E允许我们拍摄了水果的包装流程。当我们终于通过E见到B时,B问我们到底来他的果园是要做什么。我告诉B,我们在做一个艺术课题,这个艺术课题是关于国际移民劳工,以及他们长期与家人分居情况下的家庭记忆。对此,B的回答是:“只要你不是记者或者社工就行。”我曾听当地人说过B不属于那种特别容易打交道的人,但我觉得他的直白让人耳目一新。在B的农场上,国际移民劳工一天的工资抵得上他们在自己家乡牙买加辛勤工作两周的薪水。
我们接触到的第三个农场主是C,C是一个华裔加拿大人,18年前移民到加拿大。C和他的太太住在北京的时候是大学教授。3年前,他们从一个想要退休的人手中买入了这个果园。C签署购买合同后,为了在管理果园前先了解果园的运行流程,他在果园里和采摘工一起工作了三个月 。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这些繁重的工作的。在C接受果园后,他的果园产量很快翻了三倍。C总是渴望能学到关于梨子、苹果和桃子种植的最好的方法。在仅仅接手果园三年后,他的果园已经开始盈利;据我所知,这在果园产业内是很少见的。他的土地有30英亩大。他的工人住在C果场内,因为他的土地上有一幢多余的房子。C也支持我们的记录工作。
8月24日,破晓之前,我们开始跟随工人的活动。此时,工人们在做早晨的工作准备,以开启随后长达12到14小时的一天的工作。我们从他们在C农场的房子内开始跟随。早餐后,他们穿上工作服、工作靴,爬进一些改装得极简的车。这些车没有门,有一些甚至连车顶也没有。15分钟后,他们抵达B的农场(B在租用C的房子给自己的工人住)。当我们拍摄了他们早晨出发的场景后,简帮我们联系上E,这样我们可以前往水果包装的房子拍摄,并看到水果包装以供出售的流程。E 五十岁出头,很有幽默感。他允许我们进入果场拍摄,并带领我们参观果场。他向我们展示了制作箱子的机器;这种机器把二维的纸板变成三维的纸箱。他还向我们展示了审核水果的流程;比如说,如果一个桃子上有一点瑕疵,这个桃子就不能用了;或者如果一个桃子个头太小,它也没用了,所有的桃子都得是差不多的大小和形状。那些没有通过审核的桃子会被送到别处的工厂去,用来制造果酱和果脯。而前些年,这些不完美的水果是直接被丢掉的;这种做法在不久前改变了。当我看到一整墙一整墙高的、重叠起来的水果箱子时,我想,这些箱子可以成为我位于安大略省美术馆、加拿大150周年纪念展极好的素材。我想象出一个尼亚加拉瀑布的果箱替代版。E告诉我,如果我以后想用以这些果箱做艺术品,我可以联系他。然后他带我们去见了B和水果包装房内的其他工人。这是我头一次见到B。B看起来很健康,让人觉得他只有50多岁;实际上他已经超过60岁了。B有三个孩子,但是只有一个孩子继承家业,继续从事果场的工作。
我们在楼与楼之间走动,记录工人们的情况。一半的工人是西班牙的女性,另一半是本地人或者做暑假工的学生。我们在水果包装房内待了三小时。这是我第一次目击商业水果从果场到餐桌的包装过程。水果是很脆弱的,所以它们不能被长期储存,需要尽快地被送到市场上去。在当下的季节,这些水果是不能运到卑诗省去的,只能在加拿大东部销售。当水果被采摘后,它们被卡车运到包装房这边。包装的头一个工序是清洗。水果们被放在传运带上,然后花二十分钟通过一个清洗通道。然后,这些水果被带到房子内,放到一个大的托盘上;通过在托盘上的某种晃动程序,小的水果会被甩下来,大的水果被留在盘内。这些够大的水果随后被放到另外一个传输带上供工人们检查;工人们把其中没有瑕疵的放到箱子里。每一个箱子一被装满,就会被放到另一条传送带上,直接送去发货的卡车处。水果进入市场的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它们进入市场的速度越快,价值就越高,同时损耗就越少。
包装房里的所有国际移民劳工都是从墨西哥来的。他们自己人之间用西班牙语交流,也总是一起吃午饭。他们的午饭都是墨西哥菜。其中一个女性劳工把她的墨西哥煎玉米卷分了我一半,煎玉米卷味道很好,很辣。因为语言障碍,我和劳工不能非常好地交流。斯科特和顾雨可以进行基础西班牙语对话,所以他们可以和劳工交流。其中一个女性劳工通过斯科特问我,能不能把拍的他们的照片通过电邮发给他们,我说当然可以。我当晚就把白天的照片下载好,并把她想要的部分发给了她。此时,我真正开始思考,语言对于国际移民劳工在果场和本地社区(的生活)都是一个真实的障碍。大部分女性劳工年纪都是35岁到50岁之间,她们中绝大部分已经建立自己的家庭,她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供养自己的家人;她们怎样能在空闲时间学习英语呢?她们的处境让我想起了刚来加拿大时我自己的处境——那时我也不会说英文,并且有好些年一直生活在文化冲击之中。后来,我学的英语越多,我就越能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人们因为我表达能力的增强,也更加注意到我和我的艺术作品。年复一年,我逐渐融入了主流文化。这是一个终身的实践,没有捷径可走;虽然过程无比艰辛,但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学习可以慢慢做到。
我更多地思考自己刚来加拿大那段时光,那种不能说这门语言带来的感受;因为不能说英语,你不能说出自己的观点,不能理解别人的意思,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你处于社会底层的感受。那时候你完全依赖本能来尝试做对的事。有时候,你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但是你找不到对的词或者句子来表达。我依然记得,人们尝试教我发T,H和L这三个音的时候,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让自己的嘴适应这些发音。我回想着,在一个陌生的外国环境里工作,尽管你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也知道你需要做什么,但是这不是你的全部,因为你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机器的一部分。适应的过程是艰难的;它是一个很大的斗争、也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有的国际移民劳工在B的农场上已经工作了超过三十年,他们已经变成了当地社区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我们的记录,我希望人们能更多地关注到国际移民劳工,并且能用正面的态度接受他们。我们必须得承认他们;我们没有无视他们这个选项,他们必须被看到。在虚构的障碍以外,他们都是真实的人类,都有自己的希望和热情;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人要照顾。
接下来几天,我们继续从天亮跟随工人们直到他们睡觉。我们想要真正地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惯例,所以我们每天花超过12个小时一直跟着他们。从厨房开始,我们先看他们吃早饭,然后着装准备去果场;穿上袜子和靴子,他们爬上车,被送往桃树林。早晨准备出门劳作整天时工人们总是匆匆忙忙的,但是他们工作从不迟到。在桃树林间,他们系上一种特殊的、可穿戴的桶——这个桶是金属框的,里面镶着一层棉花。因为清晨露水的关系,他们在果园里穿的是透明的雨衣;虽然如此,他们的汗水最后一定会浸透他们的衣服,不论什么雨衣都不能在这方面帮到他们。他们采摘桃子的速度非常快;一棵树上一般有两个工人同时作业,工人们采摘完了一棵树,就继续采摘同一列的下一棵树。随着他们在行列间的移动,他们的车子也渐渐装满了水果。Keng是采摘工里速度最快的;同一批开始工作的工人中,他的进度总是领先于其他人。工作的时候,工人们也会互相聊天和开玩笑。另外一个采摘工,Rooster, 他话总是很多;可惜他的口音很重,我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只能猜测他是在讲故事。
10点钟的时候,工人们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很多人就会休息一下,喝点水,然后给家人打个电话。每一个人都有手机,这是他们和家人、亲朋联系的工具。10分钟的休息时间很快就到了,工人们就继续开始工作。午饭时间定在12点,工人们就会回到房间进食、让汗湿的衣服干一干。他们把短裤、靴子和袜子都脱下来,这样衣服可以在重新出去工作前干一点。视不同的日期和季节而定,他们的午餐时长介于半小时和一小时之间。今天他们的午休时间是一小时。当他们吃完午饭回去工作时,正好是一天之内最热的时候。在果园里,空气的热度让你非常不舒服、也让呼吸变得困难。在密集种植的果树间找方向并且采摘是一项让人精疲力尽的辛苦工作。下午4点的时候,工人们会再次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此时,他们看起来都非常疲惫,很多人坐在梯子上小憩。休息时间结束后,他们继续工作到晚上7点,然后回家。这是非常漫长的一天。
有几个工人年纪已经超过60岁,其他年轻一些的工人会关照这些年老的工人,年老的工人负责把小车开到水果包装房的工作。我认识了Derek,他62岁了,已经在这个区域工作了15年;他想再继续工作3年,这样他就有资格拿到加拿大养老金;Derek有三个孩子要照看。我注意到他的眼睛都是红的,他告诉我桃子的绒毛常年进到他的眼睛,对眼睛造成了伤害。我问他用哪一种眼药水,因为我想为他购买一些。Derek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休息的时候,他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桃子吃,并用他的饮用水清洗了这些桃子。清洗桃子虽然是个小的举动,但是这显示出Derek照顾他人的热情。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工人们换下衣服,冲一个澡,然后开始做晚饭。住在这幢房子里的18个人全部一起吃饭。全部人的晚饭是用一个有四个炉头的电炉做的。晚饭他们做了豆子、丝兰根薯、牙买加风味烤鸡,晚饭时做了足够的分量以供第二天早饭和午餐吃。因为现在是生产季的尾声,他们会自己做4英尺见方的板条箱,用来装采购的、带回家的东西。他们一起去采购,采购的东西包括米、烹饪油、面粉、咖啡伴侣和卫生纸。他们说,同样的东西在这边买再运回家会比在家那边买便宜很多,我简直觉得这让人难以置信。
当我看着他们把东西整理好收在板条箱的时候,我眼前构成了这样一副完整的画面:他们在农场上辛勤的劳动就等同于这些物资, 他们的劳动转变为供给家庭的物资;随着每一周的过去,他们劳动得越来越多,物资也越积越多,最终,他们带着物资回家去了。我醒悟过来,原来他们来此辛勤工作的原因就是这个——供养他们的家庭,让他们的家庭在家乡有更好的生活。这个认识让我想到中国文革期间,我在中国农村做知青的经历。我们在农村时,会买上鸡、猪肉、鸡蛋和烹饪油,然后把这些物资带回城市,因为当时城市里面临着物资短缺。那会儿中国家庭买不到保障生存所需的食物。每个月,每个家庭分配到的物资限额是0.5磅左右的猪肉,0.5升油和20磅大米。尽管处在不同的时空之中,我和这些移民劳工经历的都是生命中挣扎和艰难的时代;存在的只有现在,此刻。
每两周一次,在周四晚上,果场主会派一辆校车,把工人从居住的地方送到圣凯瑟琳斯的超市Fresh Co.,让他们一次买够两周用的物资。校车会先把劳工们送到银行,让他们从自动取款机上取钱,因为劳工都没有信用卡。超市里面有牙买加食品卖,比如芋头(Dasheen)、丝兰根薯和芋根(Cocoyam)。我们跟着工人看他们会选择哪种食物。总体来说,他们总是选择最便宜的种类和牙买加食物。购物完成以后,所有人都帮忙从窗口把食物递到巴士内,堆放好。
周六中午,安德鲁・亨特,安大略省美术馆的加拿大艺术策展人,来探访我们并看我们研究的进度如何。我非常高兴他来了。他正在策划一个明天举办的、位于安大略省美术馆的加拿大150周年纪念展,他对我这个研究很有兴趣。我和安德鲁认识20多年了,我是看着他的女儿长大的。安德鲁跟我说过,我是他育儿的榜样,因为我去博物馆和演讲时总是把女儿顾雨带在身边。我非常高兴这次能和安德鲁在农场上再聚,女儿和女婿也在身边。
我想把安德鲁和玛吉介绍给A。我们穿过他的农场时,看到他正在把新树枝嫁接到老树上。安德鲁问A,当下在加拿大做一个农场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A告诉了安德鲁文兰种植合作企业的做法是什么样的,还告诉了安德鲁,他本人的侧重点和文兰种植合作企业不同,他本人关注的是果树,以及如何能把自己的产品变得越来越好。A也提及了大多数加拿大农场主现在已经超过60岁的现状。再过10年,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大部分农场主的子辈不会再继续从事父辈的行业;现在,所有的果场工人都是国际移民劳工;A也提到,如果没有这些劳工,果园将无法运作。安德鲁和A进行了一场很棒的对话。安德鲁说,他很可能次年会邀请A去安大略美术馆做个演讲。临走前,安德鲁邀请我们参与安大略美术馆的加拿大150周年纪念展,并请我们去参观美术馆内的展览区和我作品将被展览的地方。
劳工们星期六六工作了一整天,到下午六点。晚上,本地教堂的慈善联盟组织了一次旅行,带他们去尼亚加拉瀑布。六点半的时候,我们前往劳工们居住的房子接他们。因为车内有两个空座位,我们接上了巴里和乌同。按理说车程应该只需要30分钟,但是路上非常堵。当我们停好车时,时间已经非常接近七点半,开往瀑布的船都要开了。我们一路跑着去船舶停泊处才没误船,是上船的最后几个人。在船上,每个人都穿着红色的塑料雨衣,总共有大概200个国际移民劳工和活动组织者。在顶层的甲板上,人们站成一排,都在拍瀑布;大家挤在扶手的旁边,想拍到最好的照片。红色的雨衣点缀着瀑布喷薄而下的白色浪花,看起来就像加拿大的国旗。在加拿大地标尼亚加拉瀑布, 这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视觉并置——加拿大的荣耀、壮丽与一个被大部分加拿大人忽略的群体的组合。今天,当劳工们站在船上的时候,他们走入了人们的视野——隐形的群体走到了台前,没人能够继续忽略他们。瀑布奔流而下,猛烈地冲击下方的河流,让我们身边的空气变得潮湿。当天空暗下来,灯光秀开启了;明亮的光柱打在瀑布上,五彩斑斓地、从一头打到另一头。这是一个浪漫的、梦幻得不真实的场景。当劳工们站在被照亮的瀑布前时,虽然他们看起来几乎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内,但是他们眼中饱含对现实的热情和真实。
瀑布之行的第二天是星期天。星期天是他们休息的日子。他们可以睡懒觉,所以我们早上11点才去他们住的房子。这应该是他们放松的一天,但是这一天他们用来做带回家的板条箱。我们看过工人后,驱车前往教堂。简帮我们安排了和教堂牧师的采访;简希望通过我的采访给牧师传达一个讯息——让牧师更多地帮助本地的国际移民劳工群体。我们参加了晨祷,并且听到这所教堂在哥伦比亚有一间姊妹教堂。我们看到哥伦比亚牧师被介绍参与到沉思中。仪式结束后,我们见到了牧师,问他是否愿意接受采访。牧师同意了。我们得知,牧师之前就读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内的维真神学院,并且在温哥华长大。当被问到他的教堂为国际移民劳工提供了什么帮助时,他告诉我他首要的服务对象是他的教堂会众,但他也希望有可能更多地和劳工一起活动。他说在本地社区内,有一些误解,也意识到有些事情需要被改变。
星期天晚上,恩典联合教会(the Grace United Church)筹划了一个音乐会。恩典联合教会不同于近果场的伯大尼·门诺派教堂,是另外一个组织。但这二个教会联合起来,一起在伯大尼·门诺派教堂举办了这个音乐会。从劳工们居住的房子可以步行到达教堂,所以我们所有人一起走着去。他们聘请了一个从多伦多来的三人乐队来表演。教堂里满是人、音乐和声响,我感到自己血管砰砰地跳着。音乐家走到台上去演唱。音乐会中间,一个人走上台说:“我刚刚得知我的妈妈去世了,我想为她唱一首歌,告诉她我就要回家来埋葬她了。”他饱含着感情,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听他的歌时眼中也含着泪,感受到了这个人唱歌时屋内满溢着的同情心。
29日,我们完成了在滨湖尼日加拉的拍摄,告别了劳工和果场主。简在她的房子前做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谢谢”,还在横幅边上挂上了五个国家的国旗。我们想要感谢所有的国际移民劳工、果场主和本地劳工的组织,感谢他们允许我们探访和拍摄。我们来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