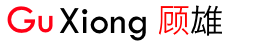近两年,我的研究和创作领域围绕着关于国际劳工在加拿大农场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在异国繁重体力劳动的枯燥循环状态中,在压抑和没有归属感的环境中的孤独情感和记忆,以及对远方家人的牵挂。
在加拿大东部以及西部,有许多来自墨西哥,尼加拉瓜,牙买加等国家的农场季节性临时工人。今年的临时工人人口已经达到三十多万,为了满足加拿大对此工种的大量需求,工人数目还在持续攀升。全球化的趋势所带来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让这一批人势必长期在这种状态下生活。
七月十二日
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菲沙流域采访过不少来自墨西哥的农场季节临时工人,也深入到他们居住与工作的地方进行实地采访考察。今年七月,我来到安大略省尼亚加拉瀑布地区,对此地区的牙买加和墨西哥工人做采访和考察。我得到了布鲁克大学美术馆馆长斯杜沃德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在我到达前,他已经帮我联系了农场季节临时工的后援委员会,于是我在到达之后便可以立即与他们联系并且开始工作。斯杜沃德先生驾车带我到附近的几个果园农场参观,在平坦的土地上看着一望无际的果园,不由让我感叹这一美景,但当我靠近果园,在果树缝隙之中看到来自外国的劳动工人时,那种反差是无比强烈的。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农场没有本地的劳动者,取而代之的却是这些外国临时工人。后来得知因为对水果的尺寸大小,包装,规格的严厉要求,农场必须要增加成本和人力,物力,才能在商业上生存,也因此,加拿大的农业产品因为价格的悬殊往往受到美国农产品的巨大冲击,所以很多本地人离开农场,搬到城市居住和工作。为了维持农场的生产规模,他们必须雇佣外国临时工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
我首先遇见了三个骑着自行车的农场工人。他们在公路的一边观看马路另一边的景象: 一个白人正在教另一位工人如何使用一辆康拜因收割机。工人们的自行车上挂着来自附近便利店买东西用的塑料袋。我们停下车,去和这些工人交谈。他们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英文交流。通过对话,我了解到他们是来自墨西哥的季节性农场工人,每年在这附近的果园里工作八个月的时间。他们每年必须获取新的工作签证,重返此地工作。他们对我说,凡是像他们这样走路或骑自行车的都是农场的季节工人。
我们到达另一处果园,那里主要种植杏树。我走进果园,随着果树摇晃的声音,隐约地看见一群工人在林间工作,他们的身影在树林中时隐时现,却总也看不清他们的脸。这情景就好像他们的现状一样,他们是在社区中被忽略,被视而不见的群体。
我下车走进杏树林,只见每个工人身着长袖长裤,大概是为了防止蚊虫的叮咬,头上也都戴了只露出面部的帽子。他们手里拿了一根长杆,正在拍打树上刚刚结果的青涩小杏子。我很吃惊,不明白为何他们要击落这好好的果子。我问了其中一位牙买加的工人,他告诉我,如果一颗果树接了太多果子,营养过于分散,整棵树上果子的质量都会受到影响。他们正在击落刚刚长出的果子,为了保证其他果子能够长得更加饱满。
我们又来到另一处杏子已经成熟的果园。此时工人们正在树下休息,吃着自己带来的午餐。有的工人吃完饭拿着手机在树下打电话,我问他们是给谁打,他们说是和家人。在不可以上网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购买国际电话卡用手机与在祖国的家人联系。
七月十三日
斯杜沃德陪我去了尼亚加拉瀑布区域每年都会有的暑期农贸集市。农贸集市是一个大型活动,附近农场的场主都可以来出售自己的农作物和自己做的食品,例如蔬菜水果,腌制的肉类和面包等。这样的农场集市是乡村农场社区情节的体现,让我看到附近农场的主人,工人,与整个社区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自己农作物,和劳动成果的热情和执着。
我们本来是要在集市见一位农场主,可是他没有出现,问了几个人,我们才找到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摊位前出售水果。他太太告诉我们今天她先生因为其他事情无法前来,她建议我们过两天去他的农场参观。后来我听说第二天集市有一个盛大的派对,将会有三千人参加,并且每个人都会带来自己最拿手的美食来参加这野餐派对。我很想去参加,但可惜第二天已经约好要去拜访农场了。
我们离开集市后,斯杜沃德开车带我去见了一个名字叫做金的女士,她经营了一个家庭旅馆,同时也是社区农场季节工人后援会的负责人。她在尼亚加拉瀑布地区很有威望,工人们都亲切的唤她为“教母”。金帮助这些工人已经有了十几年的经验了,她先后去过牙买加, 去探望这些季节性工人的家庭。金的先生罗伯特是个在当地颇有名气的音乐家,他有一个小型乐队,常常在附近演出。许多来自牙买加的农场工人都参加过他的音乐会。金向我介绍了农场季节工在她所处地区的历史,这里大部分的工人都来自牙买加,有些人已经在这里工作超过三十年。金认识几百位在附近工作的农场季节工,有的也成为了她的朋友。就在我们谈话之余,还有工人进来与她打招呼。
金告诉我,这个地区在两百年前曾经是个战场,后来变成了一个木材加工厂。再后来开始种植果树,成为专门生产桃树与杏树的果园,并且在安大略省富有盛名。可是最近十年,农场开始砍掉果树,焚烧树木,因为他们想把果林变成葡萄园。
当地的一个农场主,通过联姻与一个从香港过来的移民投资人合手在尼亚加拉地区经营旅店的投资。他的农场得到了飞速的扩展,成为了当地最大的农场主之一,而他也是砍伐果林,开始大量种植葡萄的第一人。他的举动代表的全新的农产品发展的趋势,但当地人对此颇有意见,照这样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就又会砍掉葡萄园去种植其他物种,这样频繁的转换对生态的破坏十分严重。我们稍坐片刻,因为斯杜沃德之后还有事情,我便和金女士约好第二天再来拜访她,然后同她一起去农场考察。
斯杜沃德下午要回家,也邀请我去他家作客,但他家住在离圣凯瑟琳有三小时车程的地方,我的工作必须如期进行所以我便回绝了他。他非常高兴这几天能有机会陪我到农场采访,他终于有了机会能够对社区有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研究,他或许就不会有机会有这样的体验。于是他带我回到圣凯瑟琳附近的一个租车公司租了一辆小车,这样接下来我就可以单独行动了。
七月十四日
我一大早便驾车去了金女士家,随她前往附近的农场看这地区从森林,到果林,再到葡萄园的变迁。深置其中,让我十分感慨消费文化对农业和环境的改变有着不可思议的潜在影响,人们的口味决定了农场的生产。金把我带到田野中间的用石头围起的墓地,告诉我这块墓地是这地区最老的历史记载。这块墓地目睹了两百年来这个地区的变迁。
之后,我们去了一个农场主的家,这个场主是来自瑞士的移民,在加拿大已经居住了四十年。我问他为什么移民至此,他说因为年轻想干一番事业,看到这巨大的农场十分着迷,于是便来到此地。场主的弟弟在瑞士是一位摄影师,所以一听说我是艺术家,便很高兴的与我相见。我告诉他我要采访和拍摄农场临时工人的计划, 他很爽快的答应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在卑诗省实施我的计划时,那些农场主都很冷漠,拒绝我踏入农场进行采访。对比之下他的热情,开放,让我刮目相看。他告诉我这些工人早上六点就要开始工作,并且建议我最好一早就来进行采访和拍摄,因为中午太过炎热,不适合进行这样的工作。我感谢了他的关心,也感谢他能让我第二天重返此地工作。
我告诉金我想去拍摄工人们居住的环境,于是她带我去了临时工人居住的地方,居住了大概二十多位牙买加工人的两栋在农场上的房子。金嘱咐我,不要立刻拍照,要先与他们交谈,再进一步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拍照。因为如果在他们不了解情况下就直接拍照,恐怕会引起误会。在这里,我跟一群牙买加工人慢慢的交谈,他们也对我充满好奇,问我是来做什么的。我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做一件关于临时工人的作品,明年将会在布鲁克大学展出。当我谈到我想要表现他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并开始询问他们在此地生存的状态时,一个壮年男人告诉我他从牙买加到此地已经往返三十七年了,每年都来此地工作八到十个月。每年他都做一个很大的木箱,里面装满了家庭所需的日用品和食物,这些都是他要寄回牙买加的。我很诧异,为何还要寄食物呢?他告诉我因为加拿大的东西比牙买加便宜许多。我再看到周围四处零零散散的木板,终于明白了它们的用途。看着这些木箱,再次让我想起当知青的时候,我们都会买许多农产品,肉,鸡,鸡蛋,有些腌制好,有些装进纸箱或者背篓,将它们带回家。由于那个时候在城市里物资短缺,每人每月的定量只有半斤猪肉,五两菜油,所以农产品带回去都成了稀有食品,买都买不到。
我提出想看看他居住的房间,于是他开了门,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有两张床,余外的空处都放了许多纸箱和零散的东西,他告诉我这些都是他平常攒来准备想要寄回牙买加的。墙上还有一个挂历,上面是一个妙龄妩媚的穿着三点式的牙买加美女。床上和桌子上都堆满了他的东西,上面有他的手机,日用品,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竟然还有毛绒玩具小熊,汽车等玩具。他告诉我这些是想要带回去给他的孙子的。看着这些床头的玩具,让我感觉到作为一个长辈的处境,在远方想到的只有自己的家人,这让我感到温馨。在这拥挤的临时屋内,玩具折射出所有的辛苦都是为了他们所向往的家庭正常生活。
我向他们提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你们长期在外,家里不能照顾该怎么办? 你们的性生活的需求是如何面对的?他们说,因为繁重的体力和集体居住的环境,并且也不被允许与当地的女人接触,而当地的女人也被禁止进入他们居所,如经发现,他们便会被开除。我之后再问,那你们的配偶会怎么办?会不会有其他的情人?他们告诉我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也是确实会发生的事情,但如果发生了,身处异乡,又能怎么办?
这样的境遇也曾经是我们知青当年在文革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记得那时因为自己的出身不好,并且在农村感到自己的未来迷茫,所以我对交女朋友没有任何兴趣,甚至常常感到恐惧,自己都无法养活自己,如何去组成一个家庭,让自己的孩子和我一起生活在无望之中?每想到这里,我自己都会不寒而栗。
我提出要求,让我拍一下他们的房间和肖像,他们也很爽快的答应了。当我敞开心扉跟农场工人情感上交流时,他们也很开放的谈论自己真实的状况。
之后,金告诉我她要带一个牙买加工人去流动诊所看病。我当时很惊奇,怎么会有专门为农场季节工人设置的流动诊所?就我所知,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又如何看病呢?这次要带去看病的牙买加工人被怀疑得了艾滋病,他需要去诊所做最后的确诊。诊所设立在社区原来的空房内,走进诊所,里面坐满了几十个从墨西哥,牙买加来工作的农场工。在诊所内有教授,医生,医学院学生,还有志愿者为这些工人登记,看诊,做检查。金告诉我,流动诊所是去年才成立的,这是因为农场季节工人后援会通过多年的努力,最后终于给农场工人争取到他们应有的福利。 以前没有医疗保障,如果工人出了工伤也没有伤残的补贴,只是到了最近才慢慢的有了这样的保险,但是要落实这些保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她告诉我有一个工人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左手被机器砸伤,可是伤残保险拒绝支付他伤残保险金,理由竟然是他还有另外一只手可以工作!但是因为繁琐的手续,这样的官司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才会有结果。
晚上金要去教堂参加圣经学习班,她问我可不可以去农场工人居住的地方载几个人去教堂。这些农场工人也常去教堂,在那里他们可以有和本地居民接触交流的机会。我答应了她,虽然我不是一个基督徒,也从来没有参加过教堂的圣经学习班,但为了了解农场工人的真实情景,我决定要去参加这一活动,真实的感受他们生活的各方各面。
走进教堂,我看到一共有二十几人一同来参加学习班,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农场工人。神父告诉大家今天晚上的学习主要是从五个方面了解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放了一段由圣经学院录制的录像。看完录像之后,他给每人派发了一本圣经,所有的问题都能在圣经内找到答案。之后的环节是朗诵圣经章节,最后大家各自发表讲话,谈论学习的心得和体会。 这一下触动了我对文革不可抹灭的记忆,那时候的中国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整个国家笼罩在个人崇拜的氛围中,就好像是一座巨大无比的教堂。人们每天早上要站在毛主席像前背诵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唱红歌,跳忠字舞,在现实中所有的答案都在那小小的毛主席语录本中。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很多人也叫我们去教堂,说在那里可以交朋友,学英文,我也去过一次。教堂里所进行的一切形式让我不可避免的联想到我在文革中所经历的一切,于是我再也不去了。
跟我同桌的有两个牙买加农场工人,他们对基督的见解都是联系着他们在牙买加的家庭,以及如何可以生活的更好来体现基督的价值。最后,神父开始为所有的农场工人祈祷,因为这正是收获的季节,他希望所有的农场工人都能够克服农忙季节的辛苦,困难,最终回家与家人团聚。在神父祈祷的时候,我开始细心观察这些农场工人的神态。他们十分虔诚,闭著眼睛真诚的在祈祷。我拍下了他们祈祷瞬间的照片,也祝愿他们能够承载农忙的艰辛,早日与家人团聚。宗教的仪式在他们身上非常现实的体现,那就是怎样走出现实的熬煎,获得内心的满足。
七月十五号
早上六点我就起床,空着肚子我就赶忙开车去了农场。农场主带我去了果树林,给我介绍了几位牙买加工人。我在果树林内拍摄了许多丰收的景象:成片的果树林里的杏子都红了,每一棵果树都结满了杏子,沉甸甸的把树枝都压弯了,地上也掉了许多熟透了的杏子。只见牙买加工人在树林中攀摘这些杏子,将它们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把装满杏子的篮子排成一排放在树下,等着田间的工作车来将它们运走。他们在清晨的阳光下穿梭在树林中,全身被阳光晒的黝黑。看着这些劳动中的工人,我在思考着怎样去拍摄他们。他们是一群被当地社区忽略的人群,所以我选择了从看不清他们面孔的角度去捕捉他们的身影。只有这样的画面才能展示出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现实。
太阳越来越高,我走出果树林,看到了一片玫瑰种植园地,一群牙买加工人在铲除玫瑰周围的杂草。看着他们让我又一次想起我在文革农村当中在田野上顶着烈日工作的情景。奇怪的是这种记忆会真实的再现于我的面前。他们每两个人一组,站在玫瑰的两头,共同铲除玫瑰两边的杂草,向前移动,一直到田野的尽头。我上前与他们攀谈,并且表示我想为他们拍照片,问他们是否愿意,他们都很爽快的答应了。这些工人与卑诗省的农场工人也完全不同,在卑诗省,农场工人和农场主一样,拒绝我给他们拍照,理由是担心被雇主发现就不可以再回到这里工作了。而这些牙买加的工人却很爽快,这让我感受到加拿大的东部比西部更为开放,农场主与工人的关系也更为融洽。
我在田野里转了一天,傍晚回到金女士的住处。金为我介绍了她的助手——瑞秋,她是在大学读社会学的研究生,同时也为教堂工作,经常会到农场派送信息,也与许多农场的工人十分收悉。 我与她约好第二天带我去其他的农场。金问我愿不愿意去之前提到的伤残的牙买加工人所居住的地方看望,我欣然的答应,于是我们开车去了他居住的房子。走进房屋,发现里面同样居住了十好几人。我看到伤残的男人正在准备第二天前往农场的午餐,旁边桌上有许多午餐袋。他告诉我因为手的关系,他无法再拿重物,于是只能做一些后勤的工作,比如为工人准备第二天到田间工作的食物,开车带工人们去工作的农场,和其它力所能及的琐事。 从他们居住的房子出来已是晚上十点。夜幕下的田野一片漆黑,只有房顶周围星空的光亮。房子前面停着一辆运送工人的车子,除了房间窗口微弱的灯光外,大地一片漆黑。有谁知道这些农场工在这夜幕下面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
黑暗中驾车重返圣凯瑟琳市,想到白天我在农场与工人们在烈日下一起工作,晚上却回到了假日酒店,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奇妙又奇怪。但我更想与工人们住在一起,去体验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仿佛重回我的知青岁月。
七月十六号
再次回到金家,这次看到在她的车前放有一篮新鲜的杏子。我走进门告诉她这个消息,她说这些都是农场工人路过送给她的礼物。可想而知,金这位“教母”在农场工人心目中的地位。金的助手带我沿着河边去给附近的农场工人派送广告和资料。她告诉我,每个农场的居住条件都不一样。一般来讲是十人左右住在一个房子内,但也有五十人挤在一个仓库内的情况。她告诉我一个这里的特点,那就是只要看到附近树下堆有自行车的房子,里面就一定住着这些农场工人。我问为什么?她说本地居民或农场主都是开车,只有工人才骑自行车。
我们去了前几天未能在集市上碰面的农场主的农场,这时农场主正在仓库里的一座筛选杏子的机器前面与另外两个墨西哥女工人一起工作。金的助手向农场主介绍了我,场主也同意了我在他那里拍照。这个农场主一直都在忙碌,一点都没有休息,旁边的两个墨西哥女工也一样,不断的将筛选出来的杏子装进盒子里。农场主告诉我,所有的杏子都必须超过2.5英寸以上才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这是自美国农产品的压力之下产生的新规定。因此不合格的杏子就无法在市场上出售,这规定对本地农场的损失很大,因此他们也在考虑要把果林改成葡萄园的可能性。
沿着尼亚加拉河边,我开车去了尼亚加拉瀑布,这里是全世界闻名的旅游景点,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旅游旺季,到处都是游客。瀑布飞流直下,溅起了几十米高的水花。透过阳光下的水气,我仿佛看见这些在田间辛苦劳作的农场季节工人,他们的状况就像这水气一样,在阳光下蒸发。断裂的河流成就了这壮丽的瀑布,可人们只看到瀑布雄伟的一面,没有人知道它断裂的痛苦。对我来说,这些农场工人就是河流的断层。激流从他们的身上泄下,承载着他们的辛苦的经历,对亲人的思念,情感的孤独,以及在这块新土地上的挣扎,最后流向不为人知的远方。
顾雄
2013年夏
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