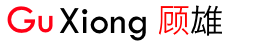约翰·奥布莱恩 John O’Brian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系教授
顾雄已经是第二次将他的作品“河流” ——他关于现代迁徙和移居的深思——装置在美术馆。[1]在两次展览中,他的作品都占据了整个房间。在温哥华的“艺说”画廊展览时,他的装置包含三个部分,由漂成白色的袜子组成的一条小径,蜿蜒穿过画廊的地面;一组用尼龙绳挂在天花板的白色石膏三文鱼,悬置于小径之上;四堵明亮的红色的墙。这是一个精简的、简约的装置。
第二次装置是在维多利亚美术馆。顾雄扩展了展览的结构,在自传的照片、消费者碎屑和漂白的棉袜子组成的小径之上,添加了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品。在这个房间里,一个明朝(1641)的铸铁寺钟,伫立在艺术家隐喻的河流里,旁边是安迪·沃霍作品《毛》的明信片;[2]一个养着猪的农房的陶器模型,是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物品,旁边放着艺术家本人和他家人在纽约世贸中心楼顶的游客照;清朝(20世纪早期)的缠脚女性穿的刺绣丝鞋,旁边放着一个孩子的塑料玩具(史努比开着飞机),这是中国制造出口美国市场的产品。[3]房间的其余部分没有变化,依然是石膏白的三文鱼,四堵明亮的红色的墙。
红与白,白与红。强烈的白,强烈的红。顾雄将极端不同的颜色并置对照,这像旗帜一样,吸引着旁观者进入装置。与此同时,它也干扰着观者的视域,并刺激着他们的情感。那强烈的红是警示的红吗,就像西方文化的交通“停”牌?还是庆祝的红——中国传统里快乐的颜色?如果红色含义的指向无法准确界定,观者可能提出问题:那它们将如何传达意义?有没有可能,它们与两种文化中一系列的意义都有关?“河流”里红白的辩证法下,有好几处让人不安紧张之处。它摇摆于欲望(爱神)与自我毁灭(死神)的两极之间,似乎塑造了一个奇怪的欲望组织。[4]“河流”展现了愉悦的希望,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种愉悦的希望下划着死亡的着重线。在中国文化中,白色是葬礼用的颜色;而拼搏回到上游产卵的三文鱼,是不会再回到海洋的。
当我第一次参观这个装置作品时,我想到,在这里,三文鱼的红色和墙壁的白色似乎对调了;仿佛鱼的红色被吸取、榨取出来,迁徙到了美术馆内部的白墙上。或者说,也有可能是墙的白色被吸出,依附在了鱼身上。曾属于三文鱼的红色被漂成了暗淡的白,曾经暗淡的白墙浸满了鲜活的红色。棉袜的白色也同样带来潜在意义上的不稳定性。对于观者来讲,棉袜的白色和红色的墙、白色的三文鱼一样,不能带来任何舒适和安全的感受。第一眼看去,袜子的纯白色似乎带来一种引人注目的纯白无暇的观感——是多么干净的白袜子啊!然而再仔细一思虑,它们也带有一种初现端倪的威胁性。这种威慑性既是种族意义上的,也是化学意义上的。人们可以想见,这些袜子浸泡在漂白剂里,经受一种仪式性的或者种族性的清洗。如果如艺术家本人所表达的,这些袜子们本意是代表着人组成的河流,那么这条河流不见得是清澈或者纯净的。[5]它也可以被解读为一条这样的河流:它洗白它所接纳的一切,扩散着致命的化学有毒物质戴奥辛(dioxin)。
在装置“河流”里,死亡的欲望驱力的暗示常常浮现出来,但是对于希望和可能的暗示也是如此。借近期出版的詹姆斯•克利福德著作《路径》中一语,这件作品集中于描写的是 “人和事物不休止的运动。”[6]水,鱼,手工品,袜子,人——所有这些都被牵扯到未完成的现代性的推拉运动中。[7]我想说,“河流”所讨论的现代性里流离失所的人,就像是一个Molson[8]的啤酒罐子(维多利亚那次装置有一个Molson的啤酒罐子),被困在一个死水旋涡里。然而这样的比喻也还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它忽略了这件装置作品里的水、三文鱼和其他成分被推动着进行的运动。它们都在朝着某个地方运动。河流是流向大海的;三文鱼是游回上游去产卵的;展览的历史文物(经历了一种文化的翻译)从中国来到加拿大——进入了维多利亚美术馆的收藏系列;那些毛的明信片和史努比的玩具是被运去给消费者的。“河流”这件装置是一个运动的叙事。
克利福德提出,“旅行”和它采用的多种形态(不仅仅指流放和强制迁徙),都是现代化多样性的决定性条件。他还提出,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人类的旅行和强制迁徙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西方”这个力量场里——既包含想象中的旅行也包含实际物理意义上的旅行。顾雄的童年成长在长江流域的重庆市。青少年的他在文革中下放到中国乡村。这与克利福德的观察一致。“当我住在中国的时候,我对于‘西方’的文化有一种浪漫的想象。我以为在北美有不限量的自由。”最近,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我想要在那里生活,从而马上获得自由。”[9]但是,当他于1989年在移民加拿大时,不仅他对于中国的希望”被碾碎了”,他发现,相较于他的想象,西方的自由更像是一种难以捕捉的商品。[10] “我对这个文化的梦想,被我自己新发现的陌生事实打破。我失去了我曾经拥有的一切。甚至连生活在母语文化里的舒适感也失去了。我在两种文化之间辗转反复,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11]
就像很多其他跨越了文化边界的人一样,顾雄被迫在加拿大改变、再造自己的身份。当然,对于一个被困在适应文化和文化僭越之间的艺术家而言,这个改变和再造的过程是持续进行的。不仅“河流”反应了这种紧张和压力,顾雄的很多其他装置也反映这个主题。他的装置《围墙》(1989)的创作时间,是在艺术家完成了班芙艺术中心的一期驻站交流、回到中国之前完成的,但这也是他长期移居加拿大之前的作品。这个装置兼行为艺术的作品是为著名的北京中国前卫艺术展而准备的。这个作品里,他把墙、地板、他穿的衣服都画上了锁链一般的网状图案,然后在中央的位置突破这个“网”。[12]《这里,那里,无论哪里》(1995)是为温哥华美术馆创作的一件大型装置作品,它绘制了顾雄从一名中国的前卫艺术家变成一个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食堂勤杂工,然后再变回一名前卫艺术家的旅程。[13]跨越边界的行为并不会终止在边界上,正如主体性的危机不会停止在自身;边界跨越和自我的撕裂,这二者一方面是顾雄经历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是现代性主体性的特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曾写道:“当今社会很少有人会没有一个正在通往别处的路上或者已经从别处回来的朋友、亲人或者同事,后者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和潜力。”[14]顾雄,就是这样行走在路上的一个人。
我之所以将这篇文章命名为《长距离泅游》,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完全可以将这篇文章命名为《浸泡在“戴奥辛”里》或者《游在放逐中》;然而,在我已经提到的原因之上,我想进一步讨论我命名的理由。[15]在我看来,“河流”不仅仅在笼统意义上提出了关于现代性和移位的问题,它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及了文化——从“泅水”这个角度。这些文化在顾雄的装置里被隐秘地代表,菲沙河代表着加拿大和“西方”,扬子江代表着中国和“东方”。
Li Xiaoping, 一位研究亚裔加拿大文化实践的多伦多作家,曾经写过“河流”装置中的“河流文化”,“扬子江和菲沙河通过太平洋的衔接得以相遇,”她观察到:“这两种文化地理的交错是通过艺术家的想象达成的。”[16]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聚集到“河流”中交错融合的是什么,碰撞的又是什么。我不能够大篇幅地对于中国江南地区的文化地理做出评论(江南地区是通向太平洋的扬子江南部的大幅地区),因为我对这个区域的理解局限于我从1998年在温哥华举办的“江南”研讨会和现代艺术展上所了解到的东西。[17](这里应该提及,“河流”就是顾雄为“江南”所作。)但是,我可以评论的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菲沙河的文化地理——这条河流呈S曲线流经该省南半部,抵达大温哥华低陆平原地区、再倾泻入乔治亚海湾。
将近250万人口居住在菲沙河及其支流灌注的区域。这条河的两岸也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所在地。同时,它也是一个被威胁着的活的有机体系。王子乔治市,在菲沙河一个弯曲处的南面一小段路程,这个弯曲处也是菲沙河流域的北部界限之一。王子乔治市是菲沙河和涅察柯(Nechako)河流交界处。作为菲沙河的支流,涅察柯河曾经有很多三文鱼——然而如今这一景象不复存在。在1950年代早期,加拿大铝业公司(Alcan)被允许在涅察柯河上建立一个水坝,并通过一个渠道将水流引向它在奇玛诺(Kemano)的水电发电厂。这个举措毁掉了这条河流;因为它带来低水位和增高的水温,并导致菲沙河上流巨大数量的鱼类死亡。尽管有这些破坏的证据存在,Alcan依然希望能扩展它自己的工业活动——如果加拿大政府给它开绿灯的话。[18]Alcan隶属的这家国际公司在全球、加拿大别处的商业扩展也成为了艺术家们作品的主题:汉斯·哈克(Hans Haacke)于1983年创作了《这里,加拿大铝业公司》(Voici Alcan, 一幅照片和文字装置),并于同年还创作了《为会议室画像》(Painting for the Boardroom)。[19]
与此同时,王子乔治市周围的纸浆和纸制品业繁荣起来——它们使用一种氯漂白水来生产产品。生产过程的工业废料(其中包含戴奥辛的化学合成物)都被倾倒在菲沙河里。戴奥辛不仅会残留在环境里长达数年,而且还被实验证明是对小鼠致癌的。菲沙河,居住在河岸的居民,更别提在河里游往上游的三文鱼和游往下游的鱼苗,他们都被迫每年容纳多达数吨的有毒物质。[20]用顾雄的艺术语言来说,这就意味着“你和我”被迫每年容纳数吨的有毒物质。
菲沙河是由生于福蒙特(Vermont)的探险家西蒙•菲沙所命名。当他“发现”这条河流时,菲沙正在为西北公司工作;西北公司雇佣他来西北地区寻找新的皮毛生产区域,以及保障有利可图的贸易站和货源路径的安全。在1807年,他在菲沙河和涅察柯河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个贸易站,并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登基后将其命名为乔治堡(Fort George, 现名“乔治王子”市Prince George )。第二年,他乘坐独木舟前往下游,由两个本地人向导和19名法裔加拿大船工陪同。尽管卡里布(Cariboo)和奇尔科廷(Chilcotin)地区原住民警告过菲沙,他还是没能为深深的峡谷和湍急的河流做好准备。他在自己的日志里写道:菲沙河是“一系列让人恐惧的、很明显难以克服的困难”。[21]当他抵达河流的一处(很可能是铁峡谷,Iron Canyon)时,他写道:“目睹如此巨大的水量如此迅疾、猛烈而不稳定地穿过这个狭隘的关卡,这种感觉非常糟。”在非常艰巨吃力的一段陆行之后,他接着写道:“讲述人们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而经历的麻烦和艰辛,将是难以置信的。”他报道说:“我们找到了塔霍廷人(Tahawteen,加拿大原住民种族之一) 称为萨斯恩(Sassian)的一种动物的角,和克里人(Cree, 加拿大原住民种族之一)称为玛雅图叶(Mayatué)的动物,也就是落基山公羊。”
我之所以引用西蒙•菲沙日志里的这些话,是因为这些话展示出他是一个密切关注自己所发现的领地的旅行者,随时警惕是否有可能遇见潜在的危险。他所叙述的故事,与顾雄在“河流”装置里的表达不同,是一种带有不确切性的叙事。菲沙的叙事既碎片化又引起人的担忧。不仅如此,他的故事还涉及到文化之间持续存在的交织、结合。菲沙提及我们找到了塔霍廷人和克里人——这仅仅是沿途帮助菲沙的原住民族中的两个;而菲沙本人是欧美裔人;菲沙随行的是法裔加拿大人,其中有一些毋庸置疑是原住民和欧裔移民的混血(Metis)。菲沙本人在记载原住民给予当地植物、动物的名字时非常地细致,这种仔细程度是跟随他的其他欧美人中绝大部分人都不具备的。
我引用菲沙的另一目的是强调制图、城镇规划和命名这些行为都给土地刻上了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意义。[22]菲沙为河流和殖民地命名的选择不是中性的。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命名行为是充满文化抹杀意味的、具有强烈政治性的行为。在他顺流而下所谓“菲沙河”之前数百年,该河流的不同地段就已经被捕鱼并生活在两岸的人们所标记和命名。而所谓“乔治堡”,在他以这个居住在地球另一端伦敦的国王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地点之前很多年,早已被赋予了一个本地的名字。这种将一种理性化的秩序强加于自然之上的行为,不过是西方所谓景观的概念;而在本地原住民文化里,这种概念是不存在的。北美的多种原住民语言里,甚至没有一个词的意义对应着英语里“景观”这个词。[23]命名这种行为,带着重复性,它并不是无害的。
加拿大原住民作为被边缘化的民族,他们对地理位置的索要权和他们的历史都曾通过命名的方式被压制。但是原住民并不是唯一受到如此待遇的民族。艾伦·海格布朗(Alan Haig-Brown)指出了一件“卑诗省被深藏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1870年代到1890年代之间,居住在奎斯雷尔(Quesnel)地区的人口中,有一半都是华人。[24]在1859年,菲沙河谷淘金热的顶峰时期,一万矿工来到了这一区域。在绝大部分金子都被淘走、淘金热消退之后,一部分华人留下来继续开采砂砾层上遗留的矿石。这些人留下的木屋直到今天都可以被看到。然而除了木屋,他们就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东西了——没有纪念碑,没有纪念物,没有地名——当地景观里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来记录他们工作的历史。这种认可的缺失在河流下游一点的地方再次重演,这次在一个叫做利顿(Lytton)的地方。1880年代,在利顿(Lytton)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铁轨的一万三千名工人里,有九千人是华人。[25]也就是说,华人足足占据了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相似的,历史在菲沙河入海口又一次重演。在入海口这里,数千名华人工作在三文鱼罐头厂,直到“一种机械的发明将他们从这个产业排除出去”。[26]罐头厂和工厂里的白人工人将这种新机器称为“铁中国佬”。至于卑诗省是如何招募到这群中国劳工,历史上几乎找不到书面的或者图像的资料。但这群华工的数量在顾雄装置作品“河流”里的迁徙三文鱼身上得到体现。二者的数量都太大以至于无法准确计量他们的数目。
这些华人劳工,穿越太平洋,来到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铁路线上工作,讽刺的是,他们却发现自己是为尚未完成的西方殖民化工作 。卑诗省是欧美扩张主义在向西扩展中的最后几个站点之一。这就是华人来到加拿大所面临的历史背景。而顾雄,在他接下来命名为“山”的多媒体装置作品中,运用铁轨和视频,探索了这一历史背景。殖民背景导致华人在卑诗省的社会架构中被双重放逐了——他们既不是主导的白人社群的一员,也不是非白人的原住民社群的一员。他们的位置是“隐形的”。“河流”这一多媒体装置质疑了殖民和抹杀的行为。它帮助我们重写了已经僵化的文化涵义。在正在进行的“去殖民化”过程中,“河流”帮助我们看清了什么是被模糊化的。
[1] 这篇论文是为凯瑟琳·海克(Katherine Hacker)所写,她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系亚洲艺术和文化的教授,以及东亚与西方关系的一位促进者。除了他们的帮助,我还要感谢戴维·古德汉姆(David Gooderham),另一位东西关系的促进者,以及温哥华的戴安·法瑞斯画廊。装置“河流”第一次展出的时候,装置用的名字是“你和我”。
[2]毛作为一个流行符号不仅仅是沃霍式的开局策略,在中国,它也是无所不在的。
[3] 在这次装置中运用的中国艺术品大部分来自维多利亚艺术馆的永久收藏。
[4] 布里俄尼·菲尔(Briony Fer), 一位对于雕塑和当代装置多有著述的研究者(例如,对居住在巴黎的黎巴嫩艺术家莫娜·哈特姆Mona Hatoum的作品的研究)提出:视域总是更倾向于愉悦而非死亡的欲望驱力。见布里俄尼·菲尔Briony Fer文章《艺术作品,心理分析作品》,收于吉尔·佩里(Gill Perry)编辑的《性别与艺术》(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240-251页)。
[5] 对顾雄本人而言,河流象征着对再生的肯定。一首顾雄为第一次装置所作的诗,开头如下:“你生于一条小溪/你长于一条河流/你于海洋中获取能量…”
[6] 詹姆斯•克利福德,《路径:二十世纪晚期的旅行与翻译》,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
[7] 近些年,迁徙这种推拉运动正在加剧。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合法的旅行和移民,非法的人类移动也在增多。国际移民组织估算,“每一年的国际贸易中,有四百万的人口‘走私’,这个产业的年价值在100亿美元。”出处:里奇·乌斯顿(Rich Ouston), 《移居》, 温哥华太阳报,1999年9月4日。
[8] 译者注:莫尔森(Molson)是加拿大的一个啤酒品牌。
[9] 顾雄,《和顾雄的对话》,收录在《顾雄:镜子:一次返回中国的经历》,白马:育空艺术中心,1999年。
[10] 顾雄,引用自佩吉·盖尔(Peggy Gale),《江南拉近了环太平洋地区》,期刊:《加拿大艺术》,1998年夏季刊,第56页。
[11] 顾雄,《和顾雄的对话》,无页码。
[12] Jin Li, 《在移位后再发现文化身份》,《这里,不是那里》(温哥华:温哥华美术馆出版,1995年),第13页。此文讨论了《围墙》这个作品与“这里,不是那里”这件作品的关系。另参考:塔妮·汉森(Tani Hansen),《品尝自由的滋味——中国的前卫艺术和艺术家》,《东方艺术报告》,IV,No.1, 1992-1993, 第41-43页。
[13]我其实应该说他”回到了新前卫艺术家”的行列。在1989年早期,中国曾一度有着变革的潜力,而顾雄,毋庸置疑的,是前卫文化组织的一份子。但是,到1995年的时候,顾雄已经生活在西方。他参与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前卫文化组织都是难以确认的了。
[14]阿尔君·阿帕杜莱, 《消失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明尼阿波利斯:明尼索达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阿帕杜莱重点强调了电子媒介正在彻底改变大众媒介的更广阔的领域,并同时改变了“想象中自我和想象中的世界的建设”。第3页。
[15] 对于某些读者来讲,《游在放逐中》会让他们联想起《游向高棉》里斯波尔丁·格雷(Spalding Gray)对于文化破裂和现代战争的反思。这种联系是我故意为之的。
[16] Xiaoping Li, 《生命之源》, 《你和我》展览手册(温哥华:“艺说”美术馆,1998年),第3页。Xiaoping Li解读说,这个展览是“极度哲学化的”,并总结道:这个展览是“对人类精神层面的存在绝不让步的肯定和坚持”。她的观点与艺术家本人不时发表的观点是相一致的。我对于这个作品的解读,与他们不同,是更加基于物质历史,而非一种哲学的个人主义的可能性。
[17] “江南”由以下个人和组织策划:西岸前沿(Western Front)的艺术家汉克·布尔(Hank Bull),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的研究生夏蔚,精艺轩画廊(Art Beatus)负责人郑胜天,王安妮 和王安妮艺术基金会,以及一系列温哥华美术馆和博物馆。
[18] 1987年,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给Alcan开了绿灯——政府签署了一个条约,同意进一步将水源疏导走。到1994年的时候,因为“保卫河流联盟”(Rivers Defense Coalition)的施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中止了这个项目。详见:贝弗·克里斯特森(Bev Christensen), 《好得不像真的:加拿大铝业公司在奇玛诺的工程结束》(温哥华:Talonbooks出版社,1995)。
[19] 关于哈克的这两件以及更多作品,请参见布赖恩·瓦里斯(Brian Wallis)编辑的《汉斯·哈克: 未竟的事业》(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出版,1986)。
[20] 参见杰夫·麦格斯(Geoff Meggs), 《三文鱼: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渔业的衰落》(温哥华:Douglas & Mclntyer出版社,1991年)。
[21] 《西蒙菲沙,信件和日志,1806-1808》,W. 凯恩·兰姆(W. Kaye Lamb)编纂(多伦多:Mcmillan出版社,1960)。
[22] “倒置的历史”,是一个由卡罗尔·佩尼(Carol Payne)组织的杰出的当代艺术展览;该展览于1997年在加拿大当代摄影博物馆展出,并讨论了这个话题。另参见:露西·利帕德(Lucy Lippard), “一言以概之” (In a Word), 收录于《本地的诱惑:多中心社会里的地方感》(The Lure of the Local: Senses of Place in Multicentered Society)(纽约:新出版社,1997)。
[23] 罗伯特·霍尔(Robert Houle),“古代人的精神遗产”,收录于黛安娜·雷米诺夫(Diana Nemiroff), 罗伯特·霍尔(Robert Houle), 夏洛特·唐思恩德-高尔特共同著作《土地,精神,权力》(渥太华:加拿大国家美术馆,1992),第61页。
[24]艾伦·海格布朗(Alan Haig-Brown), 《菲沙河》,(马德拉公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Harbour Publishing出版社,1996),第33,48页。
[25]艾伦·海格布朗(Alan Haig-Brown), 《菲沙河》,第94页。
[26] 特里·格拉文(Terry Glavin), “从旧式米厂到艾尼韦尔式打孔器(From Old Rice Mill to Annieville Drift)”, 《高低不平的地域:穿越地理景观》(温哥华:New Star Books出版社,1996),第61页。另参见:琼·巴曼(Jean Barman), 《西方以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历史》,修正版(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6),该书对“铁中国佬”一词作出了说明,并讨论了在三文鱼罐头产业里的族裔和阶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