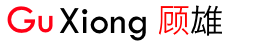安德鲁·亨特, 策展人
该文收录在顾雄“黄色河流/蓝色文明”个人展览的同名画册中。
我们一大早离开了宾馆,步行穿过一个室外的市场,买了一些水果,然后往山上走去。我们先走在马路上,然而很快就放弃了马路,选择了一条狭窄的泥路。这条泥路路过了几幢房屋。在密集的细雨中,在灰沉的天空下一片雨雾之中,我们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小山。在一阵子漫无目的的走动,以及一次寻找方向的停顿后,我们找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旧华裔公墓”。它位于一个多沙的小山上,隔着峡谷和新的大学校园对望;它的位置几乎是隐藏着的,周围修建着一些新的住宅。公墓俯瞰一条流向纸浆厂的河流。然而河流并不是它俯瞰的唯一对象;它还俯瞰着一个有力的对象,一个已经消失的过去,下方主街上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唐人街。
我们通过两座石狮守卫的铁门,走入公墓。新近重建过,公墓里有一股干净的气氛——那是尊重和骄傲的气氛。它的规划类似于圆形露天剧场。我们站在公墓下的供坛边的“舞台”上,墓碑就像“观众”一般,沿着山坡扇形铺展开来。顾雄和我分开地漫步走开。公墓里有很多新的木质的墓碑,上面装饰着简单上色的文字。我不能读中文,所以我以为这些文字都是逝者的名字;但是顾雄告诉我不是这样的。这些不是名字,是诗和祈愿。我们拍了一些照片,把水果留在了供台上,然后下山去拍了唐人街曾经占据过的地方。
山上的公墓是一股流向加拿大的黄色河流所留下的一点微弱痕迹,属于那些曾经来到“金山”谋生、想要赚钱支撑中国家人的人们。很多都打算最终返还故土却未能成行。他们无名地、不为人知地,长眠在此,是被蓝色文明消耗掉的一股黄色河流。这种命运,是顾雄很多作品的主题。早在1990年代早期,顾雄及家人就曾经对抗过这种“无名”的命运,对抗过被吞噬的可能,对抗一种用文化强加而非文化对话的方式重新定义他们生活的可能。他们担心,自己的历史和身份都将在从中国到加拿大的过渡中被抹掉。他们一家的体验是典型的移民体验:通过平衡新与旧,尝试在一个新的国家寻找自己的位置。
我过去曾写过,顾雄作品吸引我的特质之一是他艺术中博物馆式的线索。早期,他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他的作品主要是一个个人的博物馆项目,记录、收集和他自己以及自己家人有关的图像、物件、故事。然后他的注意力转移,开始融入加拿大华裔的历史存在。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作品的主题常常是受害者,是对抗着命运概率的个体和社群。在“黄色河流/蓝色文明”中,顾雄的视角更自信了。他不再是1990年代早期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食堂的勤杂工,而是同一个大学里的助理教授,同时还是一个在全加拿大、全球展出的重要艺术家。他还是一个加拿大公民,并且可以自由地前往中国。看起来,这个个人境遇的转折也反映在了他现在展览讲述的故事中。
现在,顾雄走在早期加拿大中国社群带着悲剧性的土壤上。这块土壤见证着早期铁路工人游荡失所的灵魂,允诺送这些工人回国的承诺没有兑现,唐人街存在于种族隔离中,人头税和强制的职业限制(干洗业,餐馆业和仆人)。而今天顾雄终于可以带着来之不易的信心走在这里,作为一个不仅见证了这些历史、而且可以将这些历史镌刻在公众记忆中的艺术家。而且,当顾雄回到他的“家”,也就是中国重庆时,他也可以带着同样的信心记录、重新讲述埋藏在他个人历史景观中的故事;他过去的故事中游荡着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阴魂。顾雄现在处在一个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有选择权的位置;而这个不确定的位置,就是本次作品“黄色河流/蓝色文明”所采用的位置。他做这个项目的方式,正如他之前多次使用过的方式,是通过绘制既含有诗意比喻又是生活空间的地理景观。
水是流动的,也是不稳定的。它永远都在转移着,永远处于不稳定中。无法预测又充满混乱,它可以是一股侵蚀的力量、转换的力量,一股运动、稀释的力量。作为一条河流,水可以分化和转化。它可以是一个摧毁性的、抑或是滋养性的存在。河流可以定义一个景观空间,也可以成为一个力量的源泉。被阻碍的时候,它会寻求着释放,找到另外一种途径或者采取另外一种形式。这都是顾雄对于文化的想象。
黄色河流是中国的文化,中国是顾雄的出生国。它通过不断扩展的支流流向全球。黄色河流主要是通过人的扩散而扩散,伴随着离开中国的移民人群涌入全球其他地域的城市里的他们的新家。在中国,蓝色文明总是意味着别处来的,从深蓝海域对岸的地方来的。通常,蓝色文明是一种侵略性、征服性的殖民力量,典型例子就是近代历史上的大英帝国和日本帝国。今天,蓝色文明涌入中国的主导形式,是通过西方公司的扩张。与黄色河流的流动不同,新的蓝色文明不是关于人的移动;它是由西方流行文化和产品(主要是美国的产品)的可获得性定义的,是星巴克、柯达、宜家和其他很多跨国公司现在在中国的商场定义的。
在“黄色河流/蓝色文明”里,顾雄提供了对两个强大文化力量对话的个人观点。它,在最真实的意义上,是一种当代的观点;因为顾雄作品的主题是非常“当下”的。他记录的世界是转瞬即逝的、处于不稳定中的。很多他所展示的东西可能都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这并不让人惊异。艺术永远都处于流动的状态之中,各自的影响会汇入彼此也是无可避免的;一贯就是如此。但是,今天,这种融汇的速度看起来极大地加快了,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似乎现在已经极少有静止不动的时刻;这种静止的、可以明确地定义文化和地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永恒的变化,似乎成为了唯一不变的东西。长于中国文革时期,近期才移民到加拿大,顾雄的世界始终处在一种明显的变化之中;所以顺理成章的,这种变化成为了他艺术的主题。
顾雄在此讨论的文化的巨大重合已经、并将继续引发新的文化形式。问题在于这些文化形式是否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并影响结果?城市历史学家彼得·霍尔(Peter Hall)让人信服的一个论断是:重要的文化变化常常是从一个社区或者环境以外涌入的新的观点所导致的。过去一个世纪中,中国的移民来到加拿大,他们显然对加拿大主要城市中心的面貌和这个国家不断变化中的身份作出着贡献。顾雄观察到的新的蓝色文明是很不同的;它是由涌入中国的商业企业定义的,而非人群。尽管目前还看不清楚这股蓝色文明会溺毙还是融入于黄色河流, 需要记得的是,中国在吸纳跨入它边界的东西这方面,有很长的一个历史。有迹象表明,这个传统将会继续。如顾雄所说:“黄色河流正在和蓝色文明混杂起来,流淌着一种绿色。”
就像催生本画册的展览一样,这本画册包含了顾雄过去两年里拍摄的一系列照片,有在中国拍的,也有在加拿大各地拍的。正如在甘露市艺术馆的展览一样,照片选择的流动性是由地理决定的。如果从头至尾浏览这个展览,观者就会如同从中国到了加拿大(从东到西),又从温哥华到了蒙特利尔(从西到东)。但是这个展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形式;那就会太过具体了。这个黄色河流/蓝色文明的对话,是无所不在的、也难以固定的。没有一张照片能够将它总结起来。相反,它更多地是图像的积累,是个人移动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和观察时拍摄的景象,只有以上这些能够给出最清晰的“图像”。
安德森·亨特
邓达斯市,安大略省,加拿大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