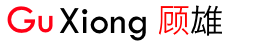与顾雄的对话
十年前你离开中国来到北美,那时的你对你的新家是否抱有任何的期望?
在我生活在中国时,我总是浪漫的幻想关于“西方”文化,想着北美那里会有无尽的自由,我想要立刻生活在那里,并且获取自由。
当我抵达时,我发现现实与我所幻想的天差地别。我为了自由来到这里,然而却在途中失去了它。我对这一文化被我新找到的怪异现实所打破了,我甚至失去了我固有文化所曾给我的安慰。我在两种文化中反复徘徊,不知我应该属于哪一边。我无法在任何一方扎根,仿佛被遗弃,被我自身无法融入二者中状态自我孤立,被排放在社会的最底层。最终,我明白了自由的真正含义,它并非给予的,它是在痛苦和困难所争取到的。
这次展览中的照片来自你在1998年去中国和你的家乡重庆的旅程,你是否认为那里有所转变?你又是否预料到了这中转变?
中国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我已经无法认出我的故乡重庆了,整个城市都在建设,旧城已经被破坏,被替换为新城,而新城的建设计划和远景与北美十分相似。中国不仅自身想要改变,但来自世界对中国施加的压力,中国也被迫必须改变。
你的照片展示了悉尼歌剧厅,伦敦大桥,自由女神像,以及其它西方标志性建筑的复制品,并且还有许多像百事,麦当劳,肯德基,万宝路香烟等象征着西方的商业主义的标志。这些都是全新的吗?
是的,这些都是全新的复制品。十年前你只能从杂志和书籍中看到它们,在90年代开始在中国露面。现在在改革十年后,西方文化和消费主义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喜欢去看这些复制品,他们想要一种似乎到过西方的感受,尤其年轻人更是认为西方的事物总会比东方的更加美好。
而西方的商业主义留下的线索却是全新的,在50年代到70年代,消费主义在革命论下面的名声是很差的。在80年代后,中国对西方开启了大门,之后这些符号便慢慢的渗入全国。我脑海中有两幅画面,一是80年代前,我们只能在中国看到无所不在的毛主席语录以及涂画,二是80年代后,随处可见的不再是毛主席,替而代之的是西方的商品符号。长时间生活于隔离中,人们开始需要新鲜的东西,他们的梦想和欲望对这些符号敞开胸怀,因为它们似乎象征着更好的生活,于是它们流行了起来。他们的来到也伴随着政治的转变。
这些照片中是否有相似性,比如不同文化中独特的部分都在统一全球文化中慢慢被退化?
它们的确成为了世界正在变为一个全球集团提供了证据。许多文化也都经历过此,但文化也可以对此有所反应,产生更深的一种改变。我们正处于在全球文化主义下面的文化进化的过程中。
你认为谁,或者什么是有责任的?大企业,通讯,还是人们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需求?
在某种方面我认为国际企业和媒体是对这样的转变有责任的。另一方面,人们也对自己本身对物质渴望的控制有责任。
你是否认为虽然亚洲有变得更加“西化”的迹象,北美却有着变得更加“亚洲化”的趋势?
亚洲国家已经变得更为“西化”了,中国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必须为了达到西方国家已经拥有的生活水准和权利而改变,而那是一条很长远的路。我没法说北美正在变得更加“亚洲化”,它是变得更加全球化和多文化,也是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所影响。强大的北美文化改变着移民,但移民也在生活中将自己所传承的文化带入这个社会和文化,这是有很多种可能的。
在某种方式中这也好像是不同文化集合的实验地。在现实中,北美比亚洲地区先进许多,或许除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以外。北美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对于我,每个国家和文化都应该有自己进步的方式,同时去了解并且与自我保持更深入交流。
我们是否在未来会无可避免的成为一个全球杂糅文化?
这是可能的。对我来说,这种杂糅文化应该包含每一种文化,它应该拥有巨大的知识,良好的通讯渠道,才能让各方面的个人性和集合性都充分融入并且被了解。这个世界文化会为每个人提供丰富的全球背景,而对统一全球文化的鉴赏会在个人实践和理解中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