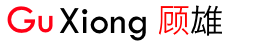我移民到加拿大菲莎河畔的温哥华已经快三十年了。明天我又要坐飞机回故乡重庆做我的展览“顾雄:移途”。这个展览就是关于在移民中,我重建自己文化身份的经历。
机场,是我每一年都要进进出出的地方。它是一个大门,分隔开非公民和公民。当我走出飞机舱门,进入候机室,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国与国的界限可以这么短,一步之遥。但这个分界线,隔不断我的思考和记忆,后二者都是延续的。一个人的经历,就是在不断跨越各种边界,穿梭于不同文化和地域中,慢慢构建起了自己的文化身份,然后这个身份不断地在充实、丰满。
我第一次来加拿大,随身带的就是一个背包、两口箱子。这就是当时我的所有。这些东西浓缩了我在中国三十年拥有的一切,是我带来展开自己生活的依据。
然而我的第一次移途,是在中国开始的。那是在文革当中,1972年初,刚刚中学毕业的我,跟成千上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一起,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而现实中,我们所有关于革命的梦想和热情,在农村——这个现实的边缘——化为乌有。每个知识青年面对的,是如何生存,如何通过劳动养活自己的问题。我和我弟弟,被下放到四川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大巴山地区。大巴山当时又偏僻、又贫穷,不通公路,没有电,甚至在山里连电台都收听不到。我们下放到清坪公社二郎沟生产队。这个村里只有两百多口人,散居在山腰各处。我们被安置在一个四合院里,与几家农户同住。对从未离家生活过的我俩,要学习的很多,比如烧麦秆做饭。附近的山已经光秃秃了,要走几十里远的山路去背柴。燃料稀缺之外,劳动很艰苦。每天天亮出工,天黑收工。生产队副队长每天吆喝着大家上工、收工。他手拿一个锣,每日在梯田间敲锣:“出工咯”,“收工咯”。然而生活的艰难、劳动的艰辛都可以忍耐,唯独思想的空虚和对前途的渺茫始终萦绕在我心中。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画速写。白天在田间休息时画农民,晚上在煤油灯下凭着记忆,纪录自己的思考,寻找自己内在的自我。慢慢地,从这些速写中,我找到了希望,渐渐接近了内在的、真实的自我。对未来的担心和无望,慢慢被对周围环境和人事的关注、自我内在的成长取代了。这是第一次,艺术带着我走出我人生的最低谷。
在农村当知青的四年里,我画了二十多本速写。今天,当我翻阅这些速写本的时候,那些画面,又把我带回了那段离我远去的岁月。我的青春都被纪录在这些速写本里面。
我第一次出国,是作为中国—加拿大交换艺术家的身份,由班芙艺术中心学院选中,在班芙做了一年的访问艺术家。没想到,这会是我人生转折的开始。彼时我对加拿大的印象,局限在七人画派和白求恩。后者还是因为文革中被要求背诵“老三篇”,其中一篇是《纪念白求恩》。1975年,加拿大的“七人画派”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展出。当我第一次看到报纸上这个展览的介绍和图片,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劳伦·哈里斯的画,画里的蓝天、雪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七人中每个画家的风格完全不同,这和文革中千篇一律的“红光亮”“高大上”创作截然相反,对我的视觉是全新的冲击。我觉得应该做那样的艺术家,画自己的画。
我在班芙从1986年9月待到1987年10月。大家现在可能对班芙国家公园熟悉,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但是对我而言,生活在班芙却像是生活在隔离区里。语言不通导致我把自己束缚在工作室里,每天埋头做作品。当时班芙艺术学院的系主任,澳文·鮑肯劝我,应该学习英文并和其他艺术家交流。他每天花一个小时教我英文。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澳文,我用蹩脚的英文对他讲:“My English is poor. ”(我英文不好。)他听了后哈哈大笑,说:“My Chinese is poor, too. ”(我中文也不好。)我一下子觉得和他拉近了距离,有一种亲近感。当时在班芙,有45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艺术家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后来我们一起去纽约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我的眼界一下开阔了。在中国只能看到印刷品的时候,看到真品对我也是一种冲击。以上种种,让我明白我应该在艺术上走自己的路。在班芙这个既美丽、又隔离的环境中,我关于“网”的艺术观念形成了,并围绕它做了一系列作品。从小型的架上画,慢慢突破为大型的壁画和装置作品、行为艺术。这一年是我在艺术上突变的一年。婉拒了系主任让我留下的建议,我带着自己的收获启程回国。
1987年回国后,我在自己的文化里竟然再次经历了“文化冲击”。我这才意识到,在加拿大的一年带给了我多大的变化。我一方面在四川美院的教学里引进了装置和行为艺术。我的课程从静物、人体开始,然后以装置、行为艺术结束,让学生体验和参与当代艺术的新形式。学生们共同创作的装置作品进入了四川美院陈列馆,作为教学成果展出,并开展了几次教学研讨会,得到了师生的正面评价。与此同时,我也参与了中国的当代艺术运动,特别是参加了1988年在成都举办的西南艺术展,1988年11月在黄山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研讨会”,以及1989年2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我的装置和行为艺术作品“网”参加了“中国现代艺术展”,并被中国日报英文版介绍。
1989年班芙艺术中心第二次邀请我作为驻留艺术家重回班芙。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但是我加拿大移民之路由此开启。飞机从上海起飞,我看着窗外,飞机飞离长江入海口,进入太平洋上空,这时眼泪夺眶而出——我的父母、妻儿、姐弟都留在了身后,不知再见何时。
移民的世界并非想象中的浪漫。语言的阻隔,思想方式的阻隔,现实极其严酷。没有运用艺术技能谋生,我选择通过洗车、做披萨、在大学食堂做清洁工来谋生。我挣扎在社会底层,也体验着社会文化和经历。在生存的同时,我坚持做自己的艺术,来表达自己生活在两种文化碰撞之下的经历,去寻找和创作碰撞之后所形成的新的空间和思考。文化身份的重建是通过面对每一天琐碎日常生活中的挑战,改变自己,学习新文化,反思固有文化而达到的。而这个过程是长期的,甚至是终生不停的。
我的艺术纪录了移民加拿大的经历,这是第二次,艺术带我走出人生的低谷,重塑了自我。我感觉这段经历使我真正成为了一个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在加拿大生活是艰难的,必须有对艺术的付出和对艺术追求的纯粹,才能走出自己的路。
回顾我的经历,我对移民的感受是:首先,须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不要怀旧,回想曾经拥有什么,因为过去的一切都不再有关,必须从零开始,获得你的追求和目标。其次,要有开放的心态,主动去学习自己陌生的东西,增进理解。若非如此,对新文化的排斥心理会让人寸步难行。这里的开放心态是双向的,是移民必须有的,也是本地居民必须有的,否则无法获得交融的状态。最后,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追求,特别是第一代移民,容易放弃自己的职业、专业。第一代移民其实蕴含着最深的文化价值,最有潜力去交融两种文化。第一代移民若能融入社会,对子女就是最好的榜样力量。我对西方文化欣赏的就是它的开放、勇气和冒险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雨过天青,总会迎来一轮明月。
明天启程回重庆,我随身带着的是自己的作品和三十年人生的体悟,它们不再是当初我两口行李箱所能承载的,它们也不是国界和飞机舱门所能阻隔的。对一个心中充满自由的人来讲,所有去过、生存过的地方,都能成为新的家。移途在继续,家的观念由此也变得更加复杂和丰满——四海为家,注定是我的命运和归宿。
顾雄
2017.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