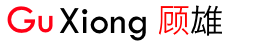她提醒我在梦里思考。
我梦见有一本速写本,里面描画出的有山水和湖泊,也许还有冰山,高低不齐的松树,起伏的花岗岩,辽阔的原野。雪,也许是雪橇,可能是一个乡村教堂,尽管小巧但却细致,铅笔和墨水悦染在灰白色的纸上。我猜这本子的封面是棕色的、厚厚的、未经漂染的画纸,它被翻开,摊在画家的双膝上,每次他展示,整理活页并重塑图象。这速写本被大家传阅,众人方能欣赏它的主人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是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从未感知过的。我见这人的手,和传阅这本子的手,同样是饱经磨练。
我又在一组大型图卷中见这场景,但这次是以油画,炭笔画,巨幅的画面,通过对片段和细节的复述,讲出一个故事。那人手握画本,一群年青人在他的周围,他指着一幅有高山的清晰画面,我即时认出那是劳伦斯 · 哈利斯作品。我就在那群年青人中,与顾雄手搭着肩在一起,指点着那幅画,中国内陆的山水随着图卷翻到后面去(那山水画仿佛出自富兰克林 · 卡迈克尔的手笔) 。每个人都在微笑;这一刻我们都以不同的眼光看世界,地貌移位, 我们的根基震动。这些图卷并不存在。
如果我的记忆正确,那是在文革高潮。一个年青人有幸从他所在的村子到北京,在北京他看了一场震憾人心的国外风景画展览,展出的作品中流露出无比的信心。作品显得那么现代,那么不受约束。年青人将这些作品精准地描绘在他的速写本里,就回去他的村子与同伴们分享,形容这些作品的气派与丰富色彩。 “这些作品甚至具有政治意义,”顾雄对我说,“但有关部门没有看出来。”他停顿了一下,向车窗外望去,巴士在一座几乎不见植物的山上行驶,狭窄的道路两侧挤满了建筑物。 “他们认为七人画派就是山水画家,想不到我们将这些作品当成是革命性的, 是自由的象征。”
我宁愿相信那本不知去向的速写本还在这世上,或许被遗忘,但我希望人们能珍惜并研究它。我想象它与别的笔记本放在一起,每本有八、九英寸大,方形,笔记本都是当年顾雄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在他当“知青”的山乡用过的。他的父母将它们收藏好,第一次来温哥华探亲的时候交还给顾雄。在一个沉思的自画像的上方,一幅红笔画成的半明半暗的肖像画,在整本以反映文化大革命英雄形象的画作中显得与众不同,顾雄曾被人扣上“太过资产阶级化”的帽子。我和顾雄最终将这些作品整理在美术馆的展厅里,作为我们探索比较中加印象的基础素材。届时有一面墙挂满七人画派的作品,顾雄在周围堆起上百件工人积极分子、英雄战士的明信片,作为对毛式国家主义宣传的对照。在墙的正中央,有一幅卡迈克尔画的加拿大地盾区域油画作为压卷之作,画中有起伏的树木和裸露的花岗岩逐渐消失在地平线外,这场景与下一展室中陈列的山中女孩的炭笔画互相呼应。
在那张绘画里,顾雨总是显得太成熟了。当年,她还很年青,大约十或十二岁,但在画中的她好似二十多岁,如同现在的她,就在洛杉矶餐馆坐在我对面。我不记得自从1997年后我是否见到过她,也许那以后在温哥华的晚餐上见过一两次,虽是如此,也是短暂的见面。 “有什么不对劲吗?”当巴士缓慢攀上重庆一条陡峭的山脊时,她这样问我,我此时已大汗淋漓。高温下的潮湿感是如此的强烈。 (也许这是1998年?)我记得一条河流,在夜晚,潮汐涨退冲着岸上陆地而来,突然一个怪浪,搅乱了波澜,将河上船只推向一边,倾覆小舟。很显然,这是罕见的现象。有人称之为“龙”。生命,在中国是如此脆弱。不久,我们分道扬镳,我从北京,经温哥华返回甘露市;而他们就一心试图拜访山中的村庄。在一个深夜渡河时,他们的小船被撞,被压在水面以下,打转并且急速下沉,被水吞没,船内空气被水挤出,仿如小艇也在奋力吸气。她被困在船里,几乎丢了性命。我记得他们回加拿大的时候给我打的电话,和看她躺在医院的照片,顾雄试图重组顾雨在温哥华水池一次溺水的经历。他将她险些遇溺的故事去寓意中国的变迁。这组图画巨大,令人难忘,其中之一,她的头几乎占了整个画面,虽然部分脸孔被漩涡遮住,她的口张开,用力吸气。又一转眼,我们在洛杉矶的小东京餐馆,面对面坐着,我想问她记不记得那个晚上,但有谁又愿意重温噩梦呢?我告诉她对我来说,现在这一切的感觉就像是零碎的记忆,所有的移动和迁徙,恒常变化和错位,自从那次旅行之后很多都已改变。
她提醒我在梦里思考。
巴士经过一条条蜿蜒在深山的隧道的入口,工人们在这里工作和起居,他们的机器设备就在入口大门的后面。这些隧道就像为这风景另写新章,是因为当年出于对西方的一种真实而困惑的恐惧,而在深山挖出四通八达的洞穴。洞穴挖出黑漆漆的空间,让人躲避从未发生的攻击,人与机器同在造梦,梦境伴随着烧焦的金属,切削液和煤油,加上肉汤和汗水的气味,裹在带有潮湿的岩石和泥土的洞里。强烈的气味从深处传出,夹杂着动物喷气和金属的气味。你会听到一声汽笛,接着黑马腾空而出,转身直奔下山。 “有什么不对劲吗?”她又一次问我,我们的巴士在坑洼的路上艰难行进。车停下来后,就看到一幅粉色纸的手写横幅,写上什么“安德鲁 · 亨特论加拿大艺术”之类的字。我每演讲一句就停下,好让顾雄翻译给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但他的翻译好像很长,也引起学生们的笑声,我不知他讲了什么。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家」从这一刻起看来很不一样。
“那次的展出对中国艺术家影响很大,”顾雄在早餐时告诉我,那是一个有和煦阳光的早晨,在棕榈树下,“所有的人都把那幅马奔向火车的作品挂在墙上,我们全明白他的作品的真意,它影响了我们很多人。”我们多次谈到加拿大的火车、蒸汽火车头、卑诗省山中那些由华工建造的险要山坳路口和隧道,他们随后定居加拿大还被阻挠,家人团聚被课以重税,他们遍布加拿大城乡,聚集在华埠,或者分散在草原和北部的小镇,开餐馆和洗衣店(只有这些是他们能合法涉足的行业) 。北美西岸是早期华人移民潮所称为的「金山」,这名词在建铁路前的淘金热时就有的。我能想象他们向山中进发的情形。
顾雨站在山顶上,华工曾在此修建过鉄路。在她的碳笔画身影中,幻想有一条铁路就在她下方,穿过河流和峡谷。她曾同父亲来到甘露市,我记得她在大学的讲台上叙述她在中国成长和移居加拿大的经历,在她新公映的纪录片「春天飞蛾」里,她的经历被进一步展现出来。我们谈到在现实与想象的世界之间漂流,随着你所带来的记忆,「他方」如何常在「这方」,就在表象之下。她讲述她与父亲合作的项目,一个探索海外劳工的生活的项目。他们的过去如何活呈现在眼前,他们记忆中的家,还有在这里的梦,在卑诗内陆、在加州、卑诗低陆平原,安省南部。给人的感觉就像真实只存在于梦中,存在于我们讲述的故事里,这种寓意式的激情便是她父亲作品的基础。一条汇集袜子与三文鱼的河流,一条蓝色文化的黄河,成千头的小猪,没有什么只是它表面所呈现,那里总有一个故事去让你发掘真相。我告诉她说:“阿利克斯 · 柯威尔说过,’作为一名优秀的现实主义艺术家,我要重塑世界。”他称他的作品是“真实的小说”。我看顾雄的作品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明白当年在北京,他和其他很多画家为何会被阿利克斯 · 柯威尔的作品所感染。 (1984, 一个好年头,让柯威尔在中国。)
我和顾雄沿着路标走到山区小城的郊外,下面是两河的交汇。我们走到大路尽头,看到一个路标,顺着记号我们上了一条窄路,穿过齐腰高枯黄的草丛和灌木来到甘露市华人墓园,那里是一个到处是木制墓碑的荒凉之处。数月后我们在温哥华岛上找到一所同类墓园,于坎伯兰镇的最外边,该镇的华埠1950年代就被夷为平地。我们将这些在加拿大城镇和山水中所作的历史记录汇集, 其中的很多地方可能就是七人画派所描绘的同一风景,曾在北京展出,甚至记在那无名画家的速写本里。当年这些画作曾启发他人,但可能还有另一层意义。这些作品出自加拿大,不仅常常出现在艺术书籍中,而且出现在介绍加拿大资源行业如采矿、林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出版物中。中国政府也许不知道这些画作启发了青年们革命性的思潮,但他们不会不知道加拿大的历史在认同大自然的同时,是和资源开发分不开的。加拿大一直是以开采自然资源之地自居,现在和中国这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并且把中国放在考虑之内。七人画派可能因而替加拿大揭示一个新的金山。
我和同事在看劳伦斯 · 哈利斯的一件作品,这作品也许是1984年北京展出的其中之一,很可能亦记录在那速写本里。我现在是「负责」保管,带着它去加州参展,设想将哈利斯展示给新一批观众,那里的人们如何评价哈利斯那粗旷的北国视角。很巧,顾雄、葛妮和顾雨这时也在加州的洛杉矶,在一个有和煦阳光的日子里,在棕榈树下,我们又聚在一起。原来大家都想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迁徙,那种没有固定居所,生活支离破碎的状况。第二天,我和顾雨再次会面。我们无话不谈,将我们相识二十年的记忆罗列在一起。顾雄和顾雨的父女关系,启发和影响了我与我女儿们的关系,她们参与了我的工作,是我的合作者。
我独自一人在开往威尔特郡大道方向的巴士上,车程远而且交通拥挤。我在车上昏昏欲睡,不记得停了多少站,一直坐到了终点站。下车即是海洋大道,我走下台阶,一脚踩到沙滩上,往海浪的方向走去。 “有什么不对劲吗?”当我走回车站又好像听到她这么问。 “我恍然体会到,”我回答她,“我想回家,但我不知何处是家。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在那一时刻我想起从二十年前我认识他们开始,一切都变了。自那时起每当我看到七人画派的作品,我就想到中国;当我想起加拿大,它的过去和未来,我就想起我和他们的谈话。从那时起我对家的感觉发生了变化,变得飘摇不定,虚无模糊,在我的思想里,加拿大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不固定的理念,一次不断变换主题的对话,一个临时性的、有时具挑衅性的个人与文化群体的对话,这对话不曾落实,也许其实已越过我们而过去了,也许是一个缺乏连贯性、凝聚力,并且已经变得模糊的故事,总之就像一个梦。
“阿利克斯 · 柯威尔的马奔向迎面开来的火车,”他惊呼,“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中国!”又一次的意想不到,在和煦阳光的日子里,在棕榈树下,我的知觉被移动,我自以为我所知道的被扰乱,一如既往,我因为这种经历而变得更加丰富。
安德鲁·亨特